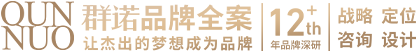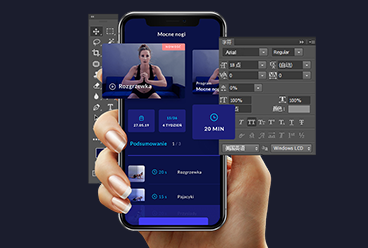如何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在梦和醒之间,一次反向制动的“示范”
无处不在的光和信息从各个方向汹涌而来
复星艺术中心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商业综合体之一——外滩BFC金融中心。步入艺术中心的展厅,透过玻璃幕墙可见对面商厦的广告荧屏闪烁,室内光滑的地面同时映照出来自天花板与展厅内作品的多处光源。无处不在的光和信息从各个方向汹涌而来——如果说玻璃外立面即是一种视觉现代性的隐喻,象征客观、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那么至少在此刻,各种认知界面的不断叠加,反而使得光滑的介质本身成为一种不透明的阻碍。

“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复星艺术中心,2023年 摄影:汪嫣然
冯至炫,《风铃-美国野牛》(2023),“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
展厅中央艺术家安德烈·穆尼亚因(Andrea Muniáin)的影像装置作品《汉娜·戴蒙德的反思》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一种与身处展厅十分类似的体验:视频动画被投影在玻璃屏幕上,和周遭事物的映像产生层层叠加,影像中,一个被透明玻璃贯穿的世界被紧紧压缩在同一个认知之幕里——甚至包括观看者自己的影像。它们共同说明,客观的、独立于观察者的“透明性”只是一种纯粹的幻想,也是一种“对所有与世界的联系中身体这一构成性介质的遗忘。”[1]正如我们不能无中介地获得“客观知识”,我们对技术的认知中也不能剥离身体这一这关键性的维度。当身体和技术处于一种互相塑造的权力关系之中,艺术将如何表征和回应这一事实,如何对这个复杂的竞争场域投来沉思性的一瞥?
3月30日,由徐震策划的全媒体艺术群展 “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开幕,展览以施政、李汉威、王梓全、佩恩恩、方阳、费亦宁、边云翔、冯至炫、善良、田翊、李昕頔、Andrea Muniáin、Lauren Lee McCarthy、Paul Chan、Tala Madani十五位艺术家的影像、装置、综合媒介作品的对话,呈现新一代中国与国际青年艺术家如何结合自身兴趣与研究领域,在算法、人工智能、虚拟世界等全新语境与挑战中,以技术反思技术,创造、发明、检验自己的反应与生命体验。
方阳,《义气诊所不营业》(2022),“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
展览入口处,李汉威的《六千万美元的人》以其巨型体量毋庸置疑地夺取人的注意力。餐桌即是云平台的象征,艺术家将其在各个网络平台上抓取的信息以实体化的“硬数据”的方式无差别地倾倒在餐桌上,观者无法一眼窥见其全貌,但从杂乱布景中抽象而出的感觉聚块有意压迫着人的注意力;与此类似,方阳的影像装置通过CG技术展现了网络狂欢和信息碎片的过度饱和;王梓全通过3D建模软件展现了一个参数化的标准世界中主体被还原为几何模型中面的动态增减,主体消亡的临界点亦是“正常”与“病态”的临界点;佩恩恩的影像装置《无尽债,逆-渲染》通过模拟手指过快滑动屏幕制造失真模糊的故障图像以达到一种“逆渲染”效果,在速度的竞争中体现出身体和技术的角力……
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和加速主义政治正积聚地掠夺和消耗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情感资源,用法国思想家伯纳德·斯蒂格勒的话来说,技术自动化造成了人的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光速的计算事件造成主体认知的短路。
劳伦·李·麦卡锡,《某人》(2019),“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
“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复星艺术中心,2023年
“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正如其标题所强调,是青年艺术家(本次参展艺术家的主体人群)对时下由技术决定论带来的焦虑情绪作出的一次集体回应。反思的决定是一次对通常是筹划性的、促逼的[2],属于技术进步主义者的技术理性模式的撤离,同时通过艺术家的技术之思将事物从对象化的、可计算的普遍命运中松脱出来,将观众的感官搅和进幽暗粘稠的技术媒介环境里。这导向了一种对于技术的不稳定的、陌异化的感知模式,即在知觉领域发生的去稳定化和解辖域化,在注意力的专注和涣散模式相继中形成异质性的时间-记忆机制,以对抗7/24小时的平台资本主义和千万兆超光速云计算事件造成知觉同质化和理性综合能力的短路。
展览非意在重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通过技术批判以复活传统人文主义的乡愁;亦不是为呈现跨学科知识协作和生产成果以弥合艺术和科技“两种文化的鸿沟”;而是悬搁了诸种判断,意图通过技术媒介返回更加幽深的、最为关键的艺术的本体论领域上来。这种返回也与当代艺术的本体论已逐渐从媒介本体论转向过程本体论息息相关:今天的技术媒介已逐渐摆脱它们的“客观”品质,在本质上成为“过程”。
施政,《熔于时间#1》(2022),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委任,“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
随着技术媒介的嵌入性越发强烈,新媒体艺术、科技艺术、数字艺术这些曾经凸显媒介特定性的专有词汇已经略显局促,因为看不见的无线网络、数据包交换、算法处理以及其他一直在我们周围发生并支撑着每一次体验的诸种计算事件,不仅仅是系统的注意力所依赖的铰链,也是我们的感知和情感生活得以传输的通道。因此,今天的艺术-技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奴辩证法式的主客关系,而是一种生态性的纠缠关系,就像哲学家提摩西·莫顿(Timothy Morton)说的网格(mesh)。艺术与其说关注的是技术媒介的特质,毋宁说更多地是关于技术对于主体的知觉、记忆和情感的塑造以及对想象力的调节方面。
正如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两幅面孔,技术的药性和毒性并存。药学式地思考艺术-技术,意味着否定性力量和肯定性力量的争夺和交替。技术既体现为新自由主义背景之下某种对身体、生命、情感进行控制的规范性,它也具备解辖域化的能力和生产性的潜能。本次展览所提出的艺术对技术的反向制动,正是对该潜能的一次试探。
费亦宁,《月之滨II: 你与我的坐标》影像静帧,2022年
王梓全,《暗处的流⾏病》影像静帧,2022年
艺术家费亦宁的动画影像讲述了在一片虚构的、由令人类失忆的拟菱形藻所占据的末日酸性海中,没有具身形态的人工智能对具有藻毒耐受能力的转基因海牛进行情感照护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对人类造成失忆的拟菱形藻和作为早期计算机储存介质的打孔卡具有相似的微观结构,这恰好是技术之药性的隐喻:作为第三持存的技术在保存了记忆的同时,又会造成记忆的丧失;而同为人造物的人工智能和藉由合成生物学技术诞生的转基因海牛之间却产生了亲密的依存关系,有机与无机、技术和自然的二分法在此消弭,技术物和生命体一同演化共存,“亲密性”在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被重新定义。
劳伦·李·麦卡锡(Lauren Lee McCarthy)则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自动化社会中的数字劳动和交互主体性的思考,邀请观众扮演人工智能管家,通过监控设备预测、理解和响应空间居住者的需求,这一方面触发了隐私方面的紧张感,引人思考技术系统的边界在哪里;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虚拟人工智能背后的非物质劳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被化约的情感性质。
善良,《耳廓狐& 灰熊》(2022),“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
除却对注意力和情感的影响,技术也深度介入着我们的时间性感知和记忆。二十世纪的时间理论和技术爆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当艺术的本体论向过程本体论转变时,主体模式也从无时间性的先验主体向过程性主体转变,这势必影响着我们的知觉组织方式和记忆机制。
Paul Chan,《第二道光》(2006),“示范:做决定技术的艺术”展览现场
在边云翔的黑白影像中,线性时间秩序发生解体,唐代士兵和二十一世纪的马拉松队员在茫茫沙漠中遇到相似的困境,仿佛是永恒轮回着的生命投来秘不可测的一瞥;施政用CGI模拟冰山崩解入海的过程,当冰块在紫色的雾气中冷漠地消融,技术时间、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的差异在此浮现;陈佩之(Paul Chan)的《第二束光》则是他的系列影像装置《七道光》的第二件作品,虽然名字带有神创论的神秘色彩,当单色光源的投影随着固定的时间间隔变幻,地上的投影展现的却是一个随着熵增变得混乱无序的世界。
这些作品展现的差异性时间叙事,可以被视为对线性时间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进步历史观念的反思,将我们引向技术和生命经验、记忆体制的深层耦联的同时,并有潜力将现代技术体制造成的普遍同质化时间政治引向异质性。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不同尺度的时间性、故意的混乱与不和谐正是对全球系统的“同步性”和单一化记忆的抵抗。